如果你還不了解班超,那么接下來(lái)小編將為大家?guī)?lái)詳細(xì)介紹。請(qǐng)繼續(xù)閱讀以下內(nèi)容:
班超,字仲升,扶風(fēng)平陵(今陜西省咸陽(yáng)市)人,著名史學(xué)家班彪的小兒子。
班超為人有大志,不修細(xì)節(jié),內(nèi)心孝敬恭謹(jǐn),居家常親事勤苦之役,不恥勞辱。能言善辯,涉獵書(shū)傳,能夠權(quán)衡輕重,審察事理。
漢明帝永平六年(公元63年),班超的長(zhǎng)兄班固被漢明帝征召到朝廷任校書(shū)郎,班超與母親一起跟隨到洛陽(yáng)生活。因家境貧寒,班超靠替官府抄寫(xiě)文書(shū)來(lái)維持生計(jì)。
班超每日伏案揮毫,重復(fù)著單調(diào)而乏味的工作,某日實(shí)在是煩了,忍不住將筆一扔,大吼道:“大丈夫即使沒(méi)有其他宏大的志略,也應(yīng)當(dāng)效法傅介子、張騫立功異域,以取封侯,豈能浸泡在筆墨間直至老死!”

周?chē)娜讼仁潜凰暮鹇晣樍艘惶?tīng)了他說(shuō)話的內(nèi)容,一起捂著肚子笑。
人家傅介子、張騫都是什么樣的人?張騫兩通西域,累功得封為博望侯;傅介子帶隨從數(shù)員出使西域,計(jì)斬不肯臣服于漢的樓蘭王,得封為義陽(yáng)侯。你能比得了嗎?再說(shuō)了,就算是你的才能堪與傅介子、張騫相比,也要有他們的際遇,得到漢昭帝、霍光和漢武帝的賞識(shí)才能展翅高飛,施展才華啊。
班超生氣地說(shuō):“小子安知壯士志哉?”為了證實(shí)自己絕非等閑之輩,他去找相面的人看相。相面的人是這樣忽悠他的:“看你的長(zhǎng)相,應(yīng)當(dāng)封侯于萬(wàn)里之外!”
“封侯于萬(wàn)里之外”,什么意思?相面的人搖頭晃腦,慢條斯理地說(shuō):“你生得燕頷虎頸,可飛而食肉,所以是萬(wàn)里封侯之相啊!”
可是,班超鵬飛萬(wàn)里的機(jī)會(huì)一直遲遲不來(lái)。直到漢明帝永平十七年(公元74年),他才有嶄露頭角的機(jī)會(huì)。且說(shuō),匈奴是秦漢以來(lái)對(duì)中原政權(quán)最具威脅的敵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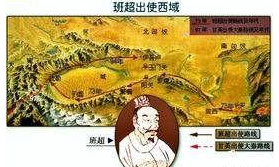
東漢初年,匈奴經(jīng)常寇略邊境,支持地方勢(shì)力控制了五原、朔方、云中、定襄、雁門(mén)五郡。光武帝鑒于建國(guó)伊始,忙于整頓內(nèi)政,穩(wěn)定社會(huì)秩序,恢復(fù)發(fā)展生產(chǎn),無(wú)力顧及。因而,在建武年間,面對(duì)匈奴連年不斷的襲擾,只是采取消極防御的方針和權(quán)且忍讓的策略,“增援邊兵郡數(shù)千人,大筑亭候,修烽火”以備匈奴,同時(shí),不斷遷邊民入常山關(guān)、居庸關(guān)以東,以避匈奴寇掠。政治上,遣使匈奴贈(zèng)送金幣以通舊好,緩和與匈奴的關(guān)系。
匈奴面對(duì)東漢這種對(duì)策,雖然間或互派使節(jié)往來(lái),軍事上仍然保持南侵之勢(shì),步步進(jìn)逼,并乘機(jī)控制了西域北道諸國(guó)。
西域東起玉門(mén)關(guān)、陽(yáng)關(guān)(今甘肅省敦煌一帶),西至蔥嶺(今帕米爾高原),中以天山分為南北二道,面積包括了今天新疆維吾爾自治區(qū)甚至更大的廣袤地區(qū)。漢武帝時(shí),朝廷派張騫通西域,并在漢宣帝神爵二年(公元前60年)前后,設(shè)立了管理西域地區(qū)的軍政合一的西域都護(hù)府,開(kāi)始了對(duì)西域地區(qū)三十六國(guó)的管轄。漢王朝先進(jìn)的科學(xué)、文化技術(shù)也由此自西域各國(guó)向西方更遠(yuǎn)的地區(qū)傳播,開(kāi)創(chuàng)了中國(guó)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,使得漢民族揚(yáng)名世界,中國(guó)的科學(xué)技術(shù)不斷地領(lǐng)先世界而又被世界所尊崇。
漢光武帝建武十四年(公元38年),西域莎車(chē)王賢和鄯善王安遣使入朝,請(qǐng)求東漢帝國(guó)派置西域都護(hù),以保護(hù)自己。
光武帝卻以“天下初定,未遑外事”為由,予以拒絕。
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(公元45年),車(chē)師前國(guó)、鄯善、焉耆等十八國(guó)派遣王子入漢都洛陽(yáng)為人質(zhì),再次請(qǐng)求派遣都護(hù),光武帝仍以“中國(guó)初定,北邊未服,皆還其侍子,厚賞賜之”,沒(méi)有同意。
從此,莎車(chē)王賢便依附了匈奴,準(zhǔn)備兼并西域。
鄯善等十八國(guó)大為憂恐,苦苦哀求漢朝將其侍子留下,并盡快派出都護(hù),以制莎車(chē)。
光武帝很無(wú)奈地傳諭:“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。如諸國(guó)力不從心,東西南北自在也。”從此,“閉玉門(mén)以謝西域之質(zhì)”。
車(chē)師、鄯善、龜茲等國(guó)也就先后投靠了匈奴。
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(公元46年),匈奴遭受到嚴(yán)重災(zāi)荒,內(nèi)部矛盾重,對(duì)東漢帝國(guó)來(lái)說(shuō),這正是剿滅匈奴的大好良機(jī),可是光武帝自覺(jué)無(wú)力發(fā)兵,最終還是放棄了。
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(公元48年),匈奴分裂為南北二部,南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,“款五原塞,愿永為藩蔽”,請(qǐng)求內(nèi)附東漢帝國(guó),以“磗御北虜”,與北匈奴對(duì)抗。
很多東漢大臣都以為天下初定,國(guó)內(nèi)空虛,南匈奴虛情假意,不可答應(yīng)。光武帝卻同意了。
他按西漢時(shí)對(duì)待呼韓邪附漢時(shí)之舊例,詔令其遷居云中郡,后又令徙居西河美稷,并通過(guò)各種籠絡(luò)措施,讓其“東捍鮮卑,北拒匈奴”,以夷制夷。
這種做法雖然在短時(shí)間內(nèi)收到了一定成效,但東漢政府每年用于安撫南匈奴的費(fèi)用極高,極大地加重了國(guó)內(nèi)人民的負(fù)擔(dān),而且北匈奴南下的攻勢(shì)卻日盛一日。
漢明帝永平五年(公元62年)至漢明帝永平十三年(公元70年)間,北匈奴猶盛,數(shù)寇邊,朝廷以為憂,“復(fù)數(shù)寇鈔邊郡,焚燒城邑,殺戮甚眾,河西城門(mén)晝閉”。
由此可見(jiàn),在北匈奴問(wèn)題上繼續(xù)實(shí)行防御政策對(duì)邊郡安定是于事無(wú)補(bǔ)的,只有“以戰(zhàn)去戰(zhàn)”,以戰(zhàn)爭(zhēng)來(lái)結(jié)束戰(zhàn)爭(zhēng),一次性地將北匈奴打趴打服,才可能得到邊境的和平。

漢明帝永平十五年(公元72年),北匈奴仍舊不知死活地頻襲邊塞。
而經(jīng)過(guò)光武帝和漢明帝父子兩代人的努力,東漢帝國(guó)國(guó)內(nèi)政治局面統(tǒng)一,社會(huì)秩序穩(wěn)定,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恢復(fù)并持續(xù)發(fā)展,百姓殷富,府庫(kù)充實(shí),國(guó)力強(qiáng)盛,已具雄厚的作戰(zhàn)潛力。
“犯強(qiáng)漢者,雖遠(yuǎn)必誅”這句話雖然出自西漢人之口,可在東漢仍舊適用!
該是出手還擊的時(shí)候了。
漢明帝永平十五年(公元72年)二月,東漢帝國(guó)兵分四路,分頭對(duì)北匈奴展開(kāi)打擊。
其中,奉車(chē)都尉竇固領(lǐng)酒泉、敦煌、張掖三郡甲兵及盧水的羌、胡兩部一萬(wàn)兩千騎,自酒泉(郡治祿福,今甘肅省酒泉市)郡直襲白山。
班超,就跟隨在竇固的軍中,任假司馬(即代理司馬),奉命進(jìn)攻伊吾,在蒲類(lèi)海與匈奴作戰(zhàn)。
該戰(zhàn)班超斬俘眾多,鋒芒畢現(xiàn),得到了竇固的青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