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古代,仕途之路是一條充滿荊棘和挑戰的道路。孟浩然,作為當時的文人之一,也經歷著這一條奮斗之路。他首先需要通過科舉考試,然后拜見丞相,最終有機會謁見皇上。這一路的艱辛和努力,構成了他仕途的歷程。每一步都是考驗,也是機遇,需要他用勤奮和智慧去征服。
此詩無關重陽,斯人不愿歸隱網傳很多關于重陽的詩中,孟浩然的《過故人莊》是一個大大的誤解,它不是重陽節的詩。
詩人孟浩然是中晚唐著名的田園詩人,和王維合稱“王孟”,他們這一派還有寫“春潮帶雨晚來急,野渡無人舟自橫”的韋應物。孟浩然是湖北襄陽人,當時來自楚湘之地的名詩人不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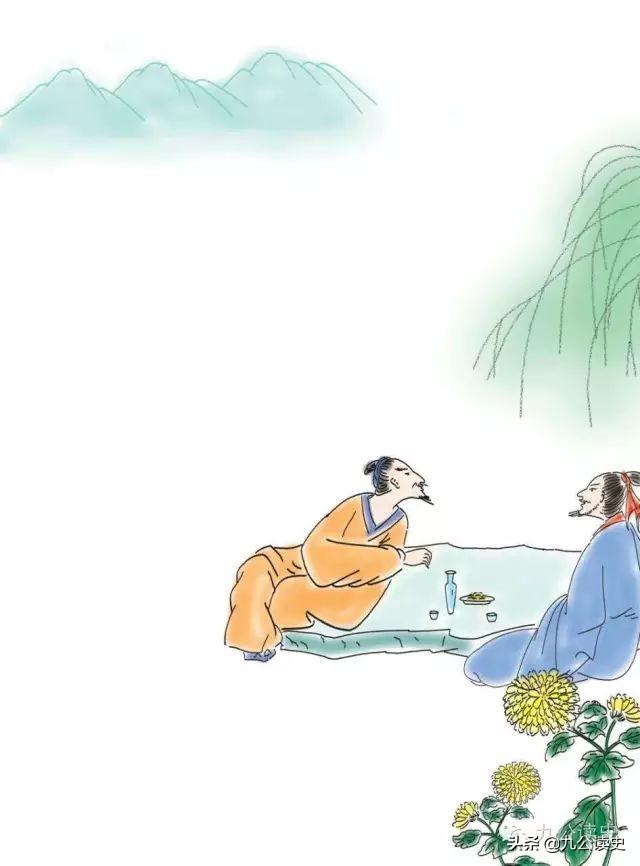
孟浩然把酒話桑麻,愜意而閑在
孟浩然的《過故人莊》確實寫到了重陽,但只是說,老朋友家的飯好菜好酒好景好,等到重陽節的時候我還要來賞菊飲酒。綠樹青山不是秋天的景致。
這是孟浩然典型的田園詩,他寄情山水田園,其實并非心甘情愿,而是情非得已,可以說,他51歲的人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追求功名,只是在屢屢碰壁之后才心灰意冷。
他是湖北襄陽這個小地方的讀書人,不斷地往京城跑,在長安這個國際大都市當北漂、做蟻族,就是為了弄一紙戶口,謀一份差事,過上體面的生活。
這是可以理解的。像孟浩然這樣的文人,必定自恃滿腹經綸,滿腔熱血,滿懷希望,努力爭取在仕途上大有作為。
否則,他除了寫寫詩,又能做什么呢?做官是古代知識分子的畢生甚至終極追求,“朝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“學好文武藝,貨與帝王家”,是他們的夢想。當時并不像今天有這么多的選擇機會。
擅長作詩拙于科舉,他的仕途路漫漫從25歲到45歲,孟浩然人生的精華部分一直在尋找機會。
一是直接參加科舉考試。有一點讓人懷疑的是,他23歲的時候,此前一直和他一起讀書學劍的張子容進京趕考,而他卻并沒有跟著去,只是去送考,而他家境尚可,應當不是盤纏的問題。
直到15年后他38歲了,才第一次到長安參考。但是命運不好,不第,沒有考上。
7年后他45歲,已經進入生命的尾聲,他再次進京趕考,但還是不第。
他的第二個求進之路是找關系托門子,叫做干謁。
這可能是當時比較流行的入仕捷徑。比如李白就找過襄陽刺史韓朝宗等很多人;朱慶余也拜見過水部員外郎張籍,還寫過一首含蓄的詩:洞房昨夜停紅燭,待曉堂前拜舅姑。妝罷低聲問夫婿,畫眉深淺入時無?您看我這樣行不行,能不能當個什么官?
孟浩然找過的人有張九齡或張說(是張九齡還是張說,歷來有不同的說法),這都是當時可以通天的中央大員。他見張九齡時也是讀書人的常規做法,寫詩表達求官入仕的心愿,但不能太直白,讀書人好面子,也怕人家不同意。
這首詩題為《望洞庭贈張丞相》:
孟浩然在詩中隱晦地希望張丞相幫他進入官場
其中求官的句子是“欲濟無舟楫”,字面上看是我要渡過洞庭湖去,可是沒有船只,其實是我要當官可是沒有路子,您能不能給我鋪鋪路?還說我“坐觀垂釣者”,看著那些在位的官員們,只有羨慕的份兒,“徒有羨魚情”。希望張丞相也能欣賞我的才華,讓我成為“垂釣者”。
可是詩寫了、遞上去了,好像沒有什么下文。
得見天顏逆龍鱗,放歸老家賦田園孟浩然35歲的時候,而立之年已經過了5年,還在仕途上毫無建樹。當年他聽到唐玄宗從長安到了洛陽,這時他還從來沒有參加過科舉,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,急匆匆地從老家趕過去。
也許他以為洛陽就是一個小鎮子,玄宗就是一個普通人,跑到那里就能見上,見上就能當官。他在洛陽一呆三年,當然是沒有結果。
他38歲進京第一次應科舉不中之后,也沒有馬上離京回鄉。這次他得以出盡風頭,寫詩名動東都,可能也讓皇帝知道了;也得以一睹天顏,終于見到了玄宗皇帝。
關于這次面君有很多說法,也有很大爭議。見面的地點有在王維家、張說家等四個說法。見到皇帝只有歐陽修編纂的《新唐書》中有記載。
這是個絕佳的機會,比他干謁任何官員都管用,但是機會來了又偷偷溜走了。
聽說皇帝來了,他嚇得趕緊鉆到床底下。但是王維不敢隱瞞,說孟浩然在我家呢。他不敢對皇上撒謊,也可能是為了給孟浩然創造機會:孟浩然到洛陽的目的就是為了見皇上。玄宗已經聽說過孟浩然的名頭,立馬叫他出來相見,還叫他把最得意的詩作拿出來欣賞。
可能從小地方鄉下來的孟浩然緊張得昏了頭,多少好詩不拿出來,出示的偏偏是這一首《歲暮歸南山》:
孟浩然惹怒玄宗,從此仕途無望
玄宗眼中期待的光隨著孟浩然的吟詠慢慢黯淡下去,生氣地說:卿不求仕,而朕未嘗棄卿,奈何誣我!你也沒有求官,說什么不才明主棄,這不是污蔑我嗎?
來自蠻荒之地的孟浩然可能穿得也寒酸,說得一口楚地方言皇帝也聽不懂。
皇帝一生氣,孟浩然的仕途就永遠斷了。可能孟浩然是自負之下的怨言,他有才學嗎?有啊,詩歌都驚動了京師啊。他求官過嗎?求過啊,剛剛參加過科舉考試啊。但是你能跟皇帝置氣嗎?皇帝永遠沒有錯,錯了也是對的。
這就像北宋柳永考進士,在詞中說不要什么浮名,而要及時行樂,仁宗一生氣,說,何用浮名,且去填詞,不錄取。所以柳永最后只得奉旨填詞,當官是沒戲了。
見玄宗可能是傳說,會作詩也不能壞制度也有說法是孟浩然根本沒有見到過玄宗。這有一定的道理,否則孟浩然這么聰明的人,此前為了進入仕途而苦苦求索,最后見到大老板怎么會干出這種傻事呢?
而且就在幾年后,孟浩然還堅持參加了第二次科舉。如果他真的得罪了玄宗,不是腦子有病,誰還會這么執著地去做這毫無希望的事呢?
唯一可以解釋的是,孟浩然確實名動一時,可能玄宗也聽說過他的名字,讀過他的詩,但是對一個高層管理者來說,他更看重制度的作用。
唐朝的科舉已經打破此前的察舉取士,有能力有才華的人即便出身寒微也可以通過考試求得功名,不能靠一兩首詩而破壞一項制度。
后來詩名遠勝過孟浩然的李白也沒有依靠作詩在朝中獲得一官半職,對玄宗來說,詩寫得好,耍耍可以,要出將入相還是差一點兒。
不才明主棄,孟浩然從此死了心,沒有戶口沒有工作的北漂之路結束,他回到老家老老實實做他的田園詩人。
仕途無望的孟浩然成了田園詩人
憤怒出詩人,但是對孟浩然來說,是恬淡出詩人。如果他去做個什么官,今天哪能讀到他這么多優美的詩呢?
文中圖片都來自網絡。轉載請注明出處,抄襲必究。更多歷史好文請關注微信公號“九公讀史”